德恒研究|税务行政诉讼中能否对已生效前置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作者:小律 发布时间:2024-06-12点击:


徐志群 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
薛亚琼 湘潭大学法学硕士
导语
税务行政争议处理过程中,如果行政相对人未对前置行政行为提起复议或诉讼,能否在后续行为的争讼中主张前置行政行为的违法性问题,法院能否审查前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而撤销后续行为,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司法实践中,此种“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问题因缺乏规范指引和学理指导,对前置行政行为能否进行合法性审查往往存在争议,各地法院在相关个案中展现出不同的审判立场和处理方式。2023年1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等联合发布中国2022年度十大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其中,儋州丰福公司与儋州市税务局那大税务分局等税务行政管理纠纷一案的裁判思维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实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典型案例
一审法院认为:1号《责令提供纳税担保通知书》和1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的前置行政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因没有适用追征期限,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虽然未被依法撤销,但在本案诉讼中上述通知书已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前置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时,就可以排除该证据的效力,即后续的行政行为没有依据。故而那大税务分局做出1号《责令提供纳税担保通知书》和1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缺乏依据,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儋州丰福公司诉请确认违法,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那大税务分局提出:一审法院排除《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效力的判决错误。《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作出后,丰福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亦未向法院起诉,应视为其对该权利的放弃。在上述前置行政行为未通过法定程序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之前,应认定其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未经法定程序而宣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无效,是对整个法律规范和行政起诉时效制度的破坏。
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税务事项通知书》虽未被依法撤销,但作为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理会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其不应被认定为1号《责令提供纳税担保通知书》和1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合法的依据。
法理分析
实际上,在其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各地法院不乏先行先试者,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适用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在肯定违法性继承思路的相关个案中,存在不同的审查方法与标准,目前主要包括告知相对人另行起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行终字第 25 号行政判决书]、在“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限度内予以审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一中法行终字第 348 号行政判决书]、在后续行政行为的争讼中予以全面审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 435 号行政判决书]和将先行行为作为诉讼证据予以审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二中行终字第 67 号行政判决书]等具体做法。
本案中,法院采取证据审的方式对前置行政行为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在税务行政行为中,前置行政行为往往表现为各种公文书证,如《税务事项通知书》《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法院认为,前置行政行为首先是一项证据,需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关联性、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并协同其他事实证据,综合判定后续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性瑕疵。当事人之间关于前置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争议,实质上是对证据证明力的争议,证明力的确定则构成了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事实附属问题。据此,法院通过将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予以合法性审查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亦展现出行政诉讼定纷止争、实现实质正义的追求。
然而,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将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加以审查应当符合证据审查的基本逻辑。本案中,法院以前置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为由排除其证据效力,实质是以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实质审查,其合理性仍有待商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证据合法性审查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指向并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在采用证据审方式对前置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司法案件中,都是以证据的标准对前置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法院无法对前置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法律适用和执法目的等方面进行实质审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613号行政裁定书]在相关案例中指出,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出发,当前置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时,人民法院应依法进行实质审查并否定其效力,即后续的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但本案中,法院并未对其排除前置行政行为效力的做法进行审慎利益平衡与充分说理论证,且税务行政案件并不同于一般行政案件,如果依据重大明显违法标准对前置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能导致纳税争议双重前置存在被规避的可能。根据《税收征管法》第88条的规定,纳税人必须在缴纳税款和提起行政复议的双重前提下才可获得税收司法救济。当可能存在纳税争议的征税事项即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提交,对于其是否先行申请行政复议,实际并不影响法院以证据标准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进行充分司法审查。但法院若以超出一般证据的标准对前置行政行为进行实质审查,则在客观上形成了规避双重前置制度的效果,从严格的形式法治意义上来说,此种灵活变通的处理方法并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法治秩序,也无法在行政相对人心目中建立起足够的信赖与支持。
法理分析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司法实践对违法性继承仍持谨慎态度,且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依据不同的审查标准对前置行政行为展开分析,可能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将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一并提出审查仍存在一定风险。
因此,当事人应注意区分前置行政行为与最终行政行为,分别判断救济途径和救济方式,在前置行政行为可诉的情形下,对于前置行政行为不服的,应积极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诉权,以避免错过司法救济的最佳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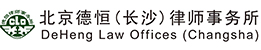



 客服1
客服1  客服2
客服2 